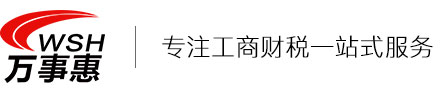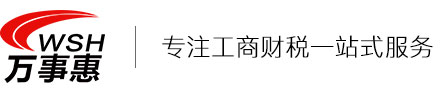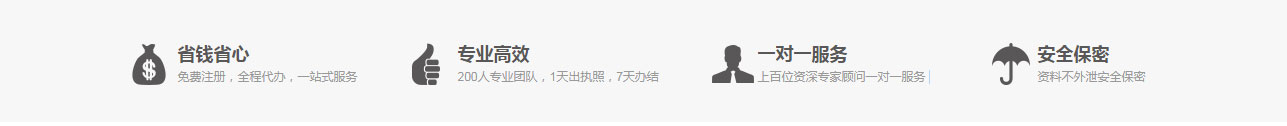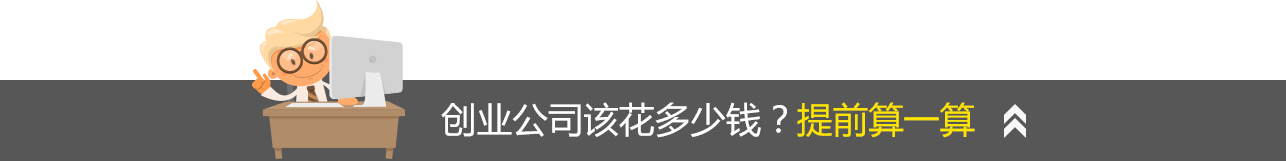中國在建立普惠金融體系方面有巨大作為空間
2020-09-02 17:01:29
今年全國兩會各方高度關注如何解決小微企業融資難和融資貴的問題,諸多代表和委員提出相關提案、議案。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提出今年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要增長30%以上。
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是世界性普遍難題,主要與成本、風險與收益不對稱有關。如果觀察歷史就會發現,中國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周期性強化也是增長方式的結果之一。
自2012年后,一系列限制地方政府融資平臺與地產業信貸政策出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浮出水面。
銀監會發布《關于2015年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明確要求實現“三個不低于”:在有效提高貸款增量的基礎上,努力實現小微企業貸款增速不低于各項貸款平均增速,小微企業貸款戶數不低于上年同期戶數,小微企業申貸獲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同時,貨幣政策加大了逆周期調節,運用結構性貨幣政策支持中小微企業。這期間,為小微企業提供服務的p2p等互聯網金融創新得到鼓勵,政府也希望通過資本市場注冊制以及針對小微企業的新三板、新四板(區域性股權交易中心)建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2018年后,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現象再次嚴峻,這與2012-2015年間發生的情況類似,即在抑制地方政府基建投資與地產業融資和擴張的同時,中小微企業首先受到影響。去年去杠桿帶來的金融收縮強化了壓力,民營上市公司也因為股權抵押融資卷入其中。
一切都似乎重復出現,原因和應對方式高度一致。如果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基建和地產作為動力,大量中小微企業就會依附在它們周圍,并形成了足夠長的復雜鏈條。當利用金融政策冷卻這兩個領域,地方政府與地產企業有強大的融資能力渡過難關,大部分中小微企業則因為市場萎縮危及生存,表現為對融資的渴求以及因風險增加而出現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
可見,自2008年以來經濟增長過于倚重基建和地產,這兩個領域又高度依賴信用擴張,即使總量的貨幣政策沒有過于明顯收縮,結構性控制這兩個領域的信貸也會給依附它們的中小微企業帶來周期性的壓力。
這說明中小微企業自身結構與整個經濟結構是高度一致的,經濟倚重基建和地產,中小微企業同樣倚重它們。如果要調整經濟結構,擺脫對基建和地產的依賴,那么,必然有大量中小微企業首先被清理。
幾乎每次救助中小微企業的金融政策首先體現在貨幣政策的逆周期調節,增加基建和地產投資,因為救助毛細血管需要給主動脈輸血。
中國只是將基建和地產投資通過不斷調控分為不同小周期,分階段利用投資的空間,形成一個長周期。或許想要通過這種控制為調整結構創造空間和時間,但市場已經認清這種周期的必然性,導致企業更樂于博弈周期,因此,每次小周期只是冷卻市場而非出清,反而不利于結構調整。
每次周期尾聲均以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作為周期調整的突破口,在貨幣政策逆周期調節同時,往往對中小微企業集中式放款,使得中小微企業信貸政策具有政策性與公益性。比如2015年的“三個不低于”以及現在要求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小微企業貸款增長30%以上。這些政策會取得一些立竿見影的效果,不過,從長期來看,還需要不斷致力于解決中小微企業日常經營中的融資問題。
中國金融供給結構的一些問題不容忽視,但這些問題與中國經濟結構匹配,而不是單獨存在。因此,經濟結構與金融結構同時推進才會有效,但經濟結構優化本身會帶來大量中小微企業的出清,產生的風險又會阻止結構調整的進行。從而形成雞生蛋、蛋生雞的難題。
即使如此,中國在建立普惠金融體系方面也有巨大有為空間,在政府層面,中國擁有國開行、進出口銀行等為大型項目和工程服務的政策性銀行,缺乏為中小微企業服務的機構。事實上,全國供銷系統有優勢、有責任為三農提供金融服務,郵政儲蓄銀行也應該在普惠金融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市場領域,以螞蟻金服為代表的金融企業大舉進入小微企業融資領域,它們擁有金融科技以及大數據形成的風控優勢,正在“攻城略地”,實現自身商業收益與中小微企業共贏的局面。不過,政府應該在該領域加強監管,因為部分互聯網金融帶有高利貸性質或帶有一定欺詐性質。
文章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